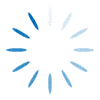约翰回来时,天色已经黑透了,肩上扛着一小袋面粉,不算沉,但他的脸色难看极了,手里紧紧抓着一份报纸,德文的。
他没多说话,只是把那张报纸默默递给她,然后走到壁炉前,背对着她,开始机械地、一块接一块地添柴。
女孩的心莫名沉了一下。
煤油灯被点亮,女孩就着跳动的光晕,展开了那份报纸。
是四天前的《人民观察家报》,边缘已经磨得起毛,沾着不知是谁留下的泥手印,头版头条是刺目的哥特体黑字:“巴黎总督冯肖尔蒂茨擅自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 军事法庭已介入调查。”
翻译过来就是,巴黎,陷落了。
是以一种“体面”的,却更让帝国震怒的方式,被放弃了。
她的目光下移,在不那么起眼的页角,还有几行小字。
“西线重组防线 警卫旗队装甲师调往荷兰参与市场花园行动防御作战。”
俞琬的手指收紧了,报纸被攥出深深的褶皱来。
警卫旗队装甲师,克莱恩的部队。
他被调往荷兰了。
就在她千辛万苦逃到这里的同时,他也来了。
“市场花园……”她喃喃重复这个陌生的词。
“盟军的空降行动。”约翰低声解释,“目标是荷兰的几座关键桥梁……想打通通往德国本土的路。”
他顿了顿,将一块木柴狠狠扔进火堆。火星腾空而起,映亮他紧绷的侧脸:“原本的一个计划是往南走,去西班牙,但现在。”他声音沉了沉,“南边的路断了,盟军推进得太快。”
他走到窗边,望着外面漆黑的天空:“先在这里住下吧,这里还算平静,暂时…是安全的。”
俞琬低下头,没有应声,只是拿起旁边一件磨破了的衣服,继续缝缝补补,针尖刺进粗布,发出单调的沙沙声。
——————
村庄外的小树林。
午后的阳光暖洋洋地洒下来,收割后的麦田一片坦荡,只留下一排排麦茬,远远望去,像是大地刚长出来的,金黄色的胡茬。
俞琬蹲在田埂边,手里拿着个小布袋,正仔细地摘着野薄荷叶,村里老奶奶咳嗽好久了,药早就用完了,她想着薄荷煮水,也许能让人舒服些。约翰又去镇上了,回来时也可以给他煮一点。
风从田野那头吹过来,裹着泥土被晒暖后的味道。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好把那些沉甸甸压着的担忧,挤出去一点点。
十天了。
躲进这个仿佛被世界遗忘的小村庄,已经整整十天了。
她不敢想克莱恩,不敢想报纸上那些语焉不详的战报,不敢想“警卫旗队装甲师去荷兰守桥”那几个冰冷的字,也不敢想桥要是守不住会怎样。
他只要能活着就好。她对自己说,指尖捏着薄荷叶,清清凉凉的香气散开来。
可念头总是不听话地飘走,如果他现在就在桥上,如果盟军的空降部队真如约翰说的会发起猛攻,如果……她用力甩头,将那些骇人的“如果”甩出去。
布袋快装满时,远处传来低沉的轰隆声。
不是打雷,那声音更沉、更钝,带着金属摩擦时的规律感,地面开始发颤,连田埂边的小石子都跳起来。
是履带碾过土地的闷响。
那感觉,她太熟悉了。在巴黎郊外覆着薄霜的训练场,在华沙的松林里,克莱恩握着她的手,贴在坦克冰冷的装甲板上,震动从掌心一路传到心口去。“这是钢铁心脏在跳。”他的声音犹在耳边。
可村长明明说过,这儿多少年都不见德国兵的影子了,一定是听错了,也许是拖拉机?或者是……
她抱着布袋心神不宁地往回走,却在村口停下了。
不对劲。平时这个时候,井边总有安妮和孩子们在跳房子,汉森太太该在门口剥豆子,老木匠该在院里敲敲打打。可今天街上空荡荡的,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连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像在躲什么似的。
“文医生!”
正奇怪着,一声细细的呼喊从柴堆后传过来。
女孩循声望去,只见安妮像只受惊的小鹿般探出头,朝她拼命招手,她心头一紧,本能地躲到柴垛后面去。那儿竟然挤着七八个村民,老人、妇女、孩子,大家都大气不敢出,齐刷刷盯着村口。
才将将挨过去,安妮冰凉的小手便一把抓住她。“外面……外面来了铁皮怪物!”
“什么怪物?”俞琬的心也跟着提了起来。
“会动的铁皮盒子,好大好大!”小女孩把手臂张到最开,用力比划着,“有这么——大!轮子是铁的,走起来轰隆轰隆!”
是坦克。
她蹲下身,把发抖的小女孩轻轻揽进怀里。“别怕,安妮,慢慢说,你看见什么了?”
“我、我在村口的树上……”安妮的蓝眼睛瞪得滚圆,“…然后就看见它们从雾里出来…好大好大,会动,声音好响…我、我吓得差点摔下来…”
俞琬的心也一揪,她搂着小女孩往柴堆后缩了缩,从缝隙里往外看。
村口的泥路上,钢铁巨兽正一辆接一辆碾进来。
虎式坦克,灰扑扑的车身上沾满泥巴,炮管低垂着,履带压过石子路嘎吱作响,每辆坦克上都站着装甲兵,黑制服,宛如中世纪的骑士驾驭着钢铁战马,闯入这片田园牧歌里来。
安妮声音抖得厉害:“它们会吃人吗?”
“它们不吃人,”俞琬轻声说,目光却无法从那个方向移开,“它们是….打仗用的东西。”
“文医生,你坐过那个吗?”安妮忽然仰起脸,害怕里竟混入了一丝孩子气的好奇。这个漂亮的黑头发姐姐是巴黎来的,爷爷说巴黎是很大很大的城市,什么都有,她该是见过这大家伙的吧?
俞琬怔住了,记忆的碎片不期然涌进来。
虽然是春日,巴黎的郊外还是很冷,克莱恩用他的军大衣将她整个儿裹住,抱进坦克驾驶舱里去,那时,他带着几分炫耀的语气说,这是刚从柏林送来测试的新型号,算是虎王的后继者。
里面又小又冷,全是机油味,男人指着那些密密麻麻的仪表盘和操纵杆:“这是炮塔转向,这是装弹机,这是……”
她冻得牙齿直打颤,缩在他怀里小声问:“开这个……是什么感觉呀?”
克莱恩笑了,是那种她熟悉的、带着几分军人痞气的笑:“想试试?”
之后他真把她按在了驾驶员的座椅上,他的温热胸膛紧贴着她后背,双手从她腋下穿过,稳稳握住操纵杆。
引擎轰鸣,坦克像一头缓缓苏醒的远古巨兽,笨重而威严地前进,她被震得东倒西歪,他却在她耳边低低地笑:“抓紧了,这还没开始呢。”
后来,他便教她认那些巨兽:四号坦克的炮塔方正敦实,豹式的倾斜装甲像猎豹弓起来的后背,虎式系列则更像一座座移动堡垒。
“豹式最快,”当时他叼着根未点燃的烟,“但也最危险,能驾驭好它的人,不是天才,就是疯子。”
“那你呢?”她记得自己仰头问他。
克莱恩没回答,只用那双如海般深邃的眼睛望着她,嘴角噙着一抹说不清是得意还是温柔的笑,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
而现在,那些被他一一指认过的大家伙,又轰鸣着闯进她的视野里来。
“坐过。”她说,声音不自觉软下来,“里面…很吵、很闷,但…也很安全。”
话音刚落,安妮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小手抓得更紧了:“刚刚,从最大的那个铁盒子里面,还、还跳下来一个人!”
俞琬的心跳倏地快了些,几乎脱口而出。
“什么样的人?”
“好高好高。”安妮踮起脚尖,小手往上比划,“比彼得叔叔还要高一大截!肩膀好宽,上面有亮闪闪的星星。”
“还有呢?”
安妮歪着小脑袋,眼睛眨巴着:“他走路的样子……背挺得直直的,像块木板似的。”
“脸呢?”女孩急急问,声音有些发颤。“看到他的脸了吗?”
安妮点了点头,不知怎的,小脸还泛起一抹浅浅的红晕来。
“他长得…好好看,像故事书里画的王子!头发是金色的,在雾里会发光,眼睛是蓝色的,鼻子直直的,嘴巴…嗯,抿得紧紧的。”
俞琬的心跳越来越快。
“但是,”安妮又缩了缩脖子,“他看着好凶,眼睛看过来的时候…冷冷的,像是要吃人,一落地就到处看,在找什么东西似的。”
金发、蓝眼,高大,气势迫人。
每听一句,俞琬的心跳就乱上一拍。不可能,克莱恩应该在荷兰的某座桥上,怎么可能忽然出现在地图上都未必找得到的这里来?
而且,金发蓝眼的德国军官…太多了,你怎么知道就一定是他?
她攥了攥小手,告诉自己别胡思乱想,却还是忍不住问。
“然后呢?他去哪儿了?”
“跟着村长爷爷,往教堂那边去了。”安妮指向村子中央那栋灰扑扑的石头房子,“他走路的样子……像爸爸量木头用的铁尺子,嗒嗒嗒的,一点不乱。”
俞琬顺着女孩的手指望过去。
距离太远,晨雾又浓得化不开,她只来得及捕捉到一个穿军大衣的背影,像惊鸿一瞥,转瞬便消失在木门后。
可那挺直的脊背,走路的步态….太像了。
这个念头刚冒头,就又被她悄悄按了回去,别犯傻,她对自己说,你只是太想他了,所以才会看到一个背影都以为是他。
“他真的去教堂了,”身边,安妮还在小声嘀咕着。“军人也会祷告吗?”
俞琬忘了答话,只是盯着那扇木门,一眨不眨,直到眼睛发起酸来,
不,不能再想下去了,他不可能出现在这里,她咬了咬唇,强迫自己转过身,拖着沉沉的步子朝农舍那边挪去,得给自己找点事做,洗薄荷叶,给老奶奶煮水,然后……
可脑子却不听使唤,那个背影总在眼前晃,安妮的话也一遍遍在耳边响,会不会,万一真是….
女孩指甲狠狠掐进掌心里,疼得她吸了口气,别期待,期待落空的时候,心里会更难过。
可刚挪到农舍门口,身后便传来村长苍老的声音:“文医生。”
老人拄着拐杖蹒跚走过来,脸上皱纹看着更深了。
“有个….德国上校,”他眼神落在她脸上,那里面盛的东西复杂极了,像有愧疚,有担忧,还有一种让人心慌的好奇,“他想见你。”
从农舍到灰石头教堂,不过短短两百米。
俞琬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那般的不真实,村道两旁门窗紧闭,但透过缝隙,她能感觉到太多双眼睛黏在她身上,害怕的,同情的,探究的。
早晨的村庄宁静得很,阳光很好,把石子路照得发白,远处田野里麻雀在叫,风车在慢悠悠地转,而她的心里像是有场风暴。
如果真的是他,第一句话该说什么?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不,听起来有点傻气。
“我….逃出来了。”好像….在说废话似的。
还是什么都不说,就像过去无数次那样,他总能在她开口前,用一个温暖的拥抱堵回她所有的话…
她摇摇头,不敢再想下去。
如果不是他呢?如果只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德国军官,例行公事询问滞留人员,再挥挥手放她离开?
那她会怎样?大概会垂下眼,乖乖回答:“是,长官”,然后转身,一步一步走回农舍,继续煮她的薄荷水,像什么都没发生。
可心里某个地方,大概会塌掉一小块。
教堂已近在眼前,刺眼的阳光下,彩绘玻璃窗上的圣徒面容被照得模糊不清。门口站着两个卫兵。
紧接着,那里面隐隐约约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隔着门版,听不清在说什么,但那冷冽、低沉的音色……
俞琬的呼吸停了一拍。
—————
村长汉森今年六十七岁,已经亲历过两场大战了,一战时,他还没成家,清清楚楚记得德国兵如何气势汹汹开进村里,抢粮食、抢牛羊、抓壮丁。
所以,当那个金发德国军官风尘仆仆走进来时,老人握紧了拐杖,做好了面对最坏情形的准备。
可那军官没要粮食,没要牲畜,对村里那点可怜的家当连看都没看。
他直接展开一张地图,用笔在上面标记了几处,便抬起头,目光凉冰冰攫住他,
“村里,有没有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年轻女人?大概这么高。”他抬手在胸前比划了个高度,“会说德语,很流利,可能……自称是医生,或者在行医。”
汉森彻底怔住了。
他没想到,德国人带着轰隆隆的坦克开进村子,第一件事不是问吃的,不是问住的,而是找人。
黑头发黑眼睛的女医生?他的脑海里立时闪过那个女孩的脸——那个总是安安静静的,会给孩子们煮姜茶,会替老人包扎伤口的东方姑娘。
为什么要找她?他脊背不由得发凉,听镇上逃难来的人说,德国人会挨家挨户抓抵抗分子,抓犹太人,抓一切“可疑分子”,那些人被带走后,便再也没回来。
“长、长官,您找的这位是……”
“她是我的人。”军官打断他,那冰冷的声线里,终于裂开一丝情绪的缝隙,像平静深海下翻腾着的暗流,“失踪了,有人看见她往这个方向来了。”
我的人,这说法太暧昧了,失踪了,又太官方了。
汉森嘴唇张了又闭,他迟疑着,不知道该说实话还是撒谎。
军官盯着他,眸色微沉,沉默了几秒,忽然向前迈了一步。
“我不喜欢重复问题。”军官声音不高,但村长活了那么多年,怎么也听出了那底下藏着的威胁,“有,还是没有?”
老人喉咙发干,他想起了那个女孩弯下腰给安妮擦汗时温柔的眼神,但他也想起自己的一家老小,想起村里这几十口人。
“有…有的。”他终于挤出声音,“但…她不像是德国人。”
军官的呼吸骤然沉了一下。
这细微的反应却被老人捕捉到了,那不像是失望,倒像一种……确认之后下意识的悸动。
“让我见她。”军官开口,语气里没有丝毫转圜余地。
“她……她现在不在村里。”汉森拄着拐杖的手在发抖,他垂下眼,却瞥见军官垂在身侧的手,竟不知何时紧紧攥成了拳头。
他在紧张。
一个手握重兵的德国上校,在一个荷兰小村庄找一个东方女人,而且…竟然紧张到指节泛白。
汉森活了六十七年,打过仗,逃过荒,第一次觉得看不懂这场战争了,可保护的本能还是占了上风,他下意识撒了谎:“她去……去隔壁的村子出诊了。”
军官没有说话,空气像是被冻住了,老人不受控地打了个战栗,下一刻,男人唇角极缓慢地向上牵了一下,眼底却没有丝毫笑意。
“老先生,”
他凑近了些,那声音像是薄薄的冰刃,贴着皮肤划过,让汉森的脸色唰得一下白透了。“我带着半个装甲连,找了三天,不是为了听你说‘她不在’的。”
“现在。”军官的呼吸喷在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你告诉我,她在哪儿?”
——————
教堂里有些昏暗,仅有的一点阳光,被彩绘玻璃过滤成了斑驳陆离的光斑,洒在石砖地面上,空气里弥散着蜡烛和潮湿石头混合的味道。这个场景太过不真实——战争、教堂、地图、和他。
祭坛前,只点着一盏小小的煤油灯,火苗不安地跳跃着。
一个人背对着门,静静站在圣坛前,黑色制服,深金色头发,肩背宽阔。
他微微低着头,手里夹着根烟。
她认得那个背影。就算隔着几个月的光阴,隔着弥漫的硝烟和一路的生死挣扎,她也一眼就认得出来。
克莱恩,真的是他。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