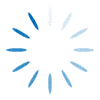身后那具滚烫的身躯还在不依不饶地蹭着,带着一种大型猫科动物求安抚时特有的带着点孩子气的固执。
池玥被他紧紧箍在怀里,耳畔是他压抑着委屈和嫉妒的低喘,后腰处那不容忽视的坚硬触感更是昭示着某种亟待解决的麻烦。她甚至能感觉到颈侧皮肤被他濡湿的鼻尖蹭得发痒。
“我对他好吗?”少女清越的嗓音带了些懒洋洋的调子,随意得像在讨论今天的雨势大不大。
墨影的动作猛地一顿。
他像是没料到她会这么问,埋在她颈窝的脑袋微微抬起,熔金色的瞳孔在昏暗室内闪烁着困惑的光。
池玥并没有等他回答,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语调平缓。
“我让他住在随时可能炸炉的侧室,一天之内炸了两次炉,差点毒晕自己,我还警告他再炸就丢去喂灵猿。这叫好?”
她微微偏过头,几乎能感受到他炽热的呼吸喷洒在脸颊上。
“我把他用绳牵着掉在飞剑后面,让他在百米高空上方尖叫。这叫好?”
墨影喉咙里发出一声极低的呜咽,像是想反驳什么,却又被这列举的事实噎住了。
“还是说,”池玥轻轻叹了口气,那口气息拂过他的锁骨,带着点无奈,“我让他浑身湿透,像个落汤鸡一样跟在我身后,在旁人暧昧的眼光里,住进西厢那间连炭火都没烧起来的冷屋子,就叫好?”
她每说一句,身后那个紧绷的身躯就软下一分。那双原本死死箍在她腰间的手臂,力道也悄然松懈了些许。
“可是墨影,”她忽然转过身来,双手抵在他赤裸的胸膛上,微微仰起脸,那双清凌凌的眸子直直望进他有些慌乱的金瞳里,“我允许你在我榻上酣睡,甚至枕着我的体温入睡。”
“我将自己的鲜血喂给你,让你打上我的烙印。”
“我纵容你毁了我的洞府大门,在我的地盘上留下抓痕。”
“我把你贴身带着,连去见掌门……都未曾将你取下。”
她的声音不高,却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敲在他的心上。
“我对你的‘好’和‘包容’,是允许你放肆,允许你靠近,允许你像现在这样,对我予取予求。”
她指尖轻轻点在他脖子上那道青色的契约印记上,那里正随着她的话语而发烫。
“而你,却觉得我对一个连靠近我都需要我撑伞、被我一句话就吓得同手同脚、连反抗都不敢的药罐子……”
她顿了顿,唇边终于浮现出一抹极淡、却带着某种洞悉一切的了然笑意。
“是‘好’?”
最后的尾音带着一丝疑问,仿佛真的在困惑他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比较。
墨影彻底僵住了。
那张总是写满凶戾与暴躁的脸上,此刻只剩下一种近乎呆滞的茫然。金瞳里的火焰渐渐熄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巨大的、迟来的认知冲击后的眩晕感。
他顺着她的指尖低头,看向自己脖子上那道烙印。那是她赐予的,独一无二的。她又指了指他颈侧,那里有一道更隐秘的、属于昨日她指尖划过留下的淡淡红痕。还有他腰腹间,那些在守护洞府时被她踹到留下的、还未完全消退的印记。
这些……都是她留下的。
都是“属于她”的证明。
而那个药罐子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身湿透的、散发着苦涩药味的衣服,和一本同样湿透的破笔记。
一种混杂着狂喜、羞耻、以及被彻底看穿的狼狈情绪,如同海啸般席卷了他。
原来——是这样。
原来她并非对那个废物另眼相看。她只是在履行“主人”的义务,仅此而已。
而对他……才是真正的、毫不掩饰的……纵容与独占。
巨大的满足感瞬间淹没了方才那股几乎要将他焚烧殆尽的妒火。他喉结滚动,想说些什么,却发现自己喉咙干涩得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能像个傻子一样,呆呆地看着她。
池玥看着他这副从张牙舞爪的猛兽瞬间变成被顺毛撸傻了的家猫模样,心中那点无奈又好笑的情绪更盛了。
果然,猫科动物的脑仁,就算成了剑灵,恐怕也……嗯,有待商榷。
她不再多言,抬手揉了揉他那一头略显凌乱的黑发。
“现在,”她收回手,语气恢复了平日的清冷,只是眼底那点笑意尚未完全褪去,“可以安静下来,好好谈一谈你今晚到底想要什么了吗?”
她说着,目光意有所指地向下扫了一眼,落在他那处依旧精神奕奕、昭示着主人并未完全“消气”的地方。
墨影顺着她的视线低头,脸上那层刚消退不久的薄红瞬间以更汹涌的态势卷土重来。
他张了张嘴,那句在喉间翻滚了许久的、充满了兽性与渴望的“要你”,此刻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磨人也更加滚烫的羞耻感。
他想要她。想得发疯。想用最原始、最粗暴的方式确认她的归属。
但此刻,在刚刚被她用那样“清晰明了”的方式“哄”过之后,那些野蛮的念头,似乎都变得……不够“好”了。
他想要一种更配得上她这份“纵容”的“好”。
那股子令人头皮发麻的热度顺着脊椎一路烧到了耳根。墨影低垂着头,视线在那双踩在柔软地毯上的赤足周围游移,竟不敢再往上哪怕一分。先前那股子要将人吞吃入腹的凶狠劲儿,此刻全化作了不得不低头的局促。
喉间那块软骨艰涩地滑动了几下,却发不出半点声音。
满腹的辩驳在这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那道烙印在脖颈发烫,像是一记无声的耳光,抽得他那点可笑的嫉妒心支离破碎,只余下满地名为“被偏爱”的狼藉。
原来,那并非施舍。
那条总是爱出风头的长尾此刻也没了精神,焉哒哒地垂在身后,尾尖在地毯那繁复的花纹上无意识地画着圈,像个犯了错被抓现行的孩童。原本紧绷如铁的肌肉线条柔和下来,透出全然臣服后的松弛。
“属下……知罪。”
良久,他才从齿缝间挤出这几个字,声音闷在胸腔里,带着点不易察觉的鼻音。
那双总是习惯于掌控杀戮的手,此刻有些笨拙地抬起,指尖轻颤着,触碰到了自己腰间那条早已松垮的系带,缓缓单膝跪下。随着动作,那层薄薄的布料滑落,那处早已按捺不住的昂扬毫无遮掩地弹跳而出,在昏黄烛火下泛着充血的深红光泽,青筋蜿蜒其上,狰狞中透着股亟待安抚的渴望。
这便是他的回应。赤裸,直接,却又卑微到了尘埃里。
但这还不够。
仅仅是献上这具皮囊,似乎已配不上那份沉甸甸的“纵容”。
墨影那双金瞳微微眯起,瞳孔深处流转过一抹暗沉的幽光。周遭原本静谧的阴影忽然变得粘稠起来,仿佛有了生命般缓缓蠕动。几缕漆黑如墨的气息从他脚底延伸而出,带着杀意的尖锐突刺熔融化作了柔韧无骨的幽暗触须,顺着那垂落的床幔无声向上攀援。
没有实体的触须尖端,带着股沁入骨髓的凉意。它们极其小心翼翼地探入那袭宽松道袍的袖口与裙摆,如灵蛇般蜿蜒而上,最终虚虚地在皓腕与脚踝处绕了一圈,凝结成几道似真似幻的黑色圆环。
“若是,这般呢?”
他终于抬起头,那张苍白俊美的面容上不再有半分戾气,只余下一种近乎献祭般的虔诚与狂热。他膝行上前,那具精壮赤裸的身躯在阴影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具有张力。
那双手并未直接触碰那处圣地,而是撑在池玥身侧,将她整个人圈在自己与床榻之间。
“既是予取予求。”
他唇角勾起一抹极淡却带着些许邪气的弧度,那条长尾从身后探出,尾尖卷着一枚也不知从何处顺来的、尚且带着露水的海棠花瓣,极其轻佻却又郑重地抵在了她那微启的唇瓣之上。
“那便请主人,试一试这把‘凶剑’的……另一面。”
那一点微凉的花汁在唇齿间炸开,带着苦涩后的回甘。
墨影起身,俯首,极其耐心地用舌尖描摹着她的唇形,将那点残余的花汁一点点舔舐干净。那舌面特有的倒刺被他刻意收敛,只余下粗糙却温热的触感,刮擦过娇嫩唇瓣,带起一阵细密的酥麻。
那些缠绕在四肢上的黑影微微收紧。那力度拿捏得极好,既让人感受到那份不容忽视的掌控欲,又不至于勒痛半分,倒像是多了一层冰凉顺滑的肌肤。
这种被完全包裹、被细密掌控的感觉,正如同一张精心编织的网,将两人隔绝在这方寸天地之间。
他那一手仍撑在身侧维持平衡,另一只手却极其大胆地握住了她搭在他肩头的那只手,引着那微凉指尖一路向下,划过滚动的喉结、起伏的胸肌、紧绷的腹直肌,最终停在那处滚烫的坚硬之上。
“……这里。”
他眼尾泛红,声音低哑得几不可闻,带着明显的诱哄,“若是觉得……不听话,便……罚它。”
那话语里的“罚”,听在耳中,分明就是求抚慰的另一种说法。
当指尖真的触及那处时,墨影整个人猛地一颤,喉咙里溢出一声压抑不住的闷哼。他像是被抽去了所有力气,重重地将额头抵在她肩窝处,大口喘息着,任由那只手掌握住他的命脉。
那根肉柱在他意念的催动下,竟极细微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本光滑的表面浮现出些许暗金色的纹路,温度更是烫得惊人,甚至在顶端那个小孔处,极其羞耻地溢出了一滴透明的清液,蹭在了她的掌心。
那份掌控感似乎彻底击碎了他最后一道防线。
墨影那条长尾再也维持不住方才的矜持,顺着她的小腿蜿蜒而上,冰凉的金属环扣紧贴着肌肤,与他那处火热的体温形成鲜明对比。他腰身不受控制地向前挺送,一下又一下,极其淫靡地在那只手中抽插磨蹭,试图获取更多的抚慰。
那双原本凶狠的金瞳此时已是一片水雾迷蒙,眼角那抹绯红艳丽得惊人。他仰着颈项,脆弱的喉结完全暴露在空气中,随着急促的喘息上下滚动,像是在无声地邀请着什么。
“剑、已出鞘。”
他语无伦次地低喃,那声音里夹杂着某种破碎的快意与极致的渴望,“请主人,试剑。”
这一刻,他不再是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巡守者,也不再是那只只会吃醋炸毛的大猫。
他仅仅是一把渴望被使用、去填满、被彻底打磨的兵刃。
而握剑的人,只有她。
唯有她。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